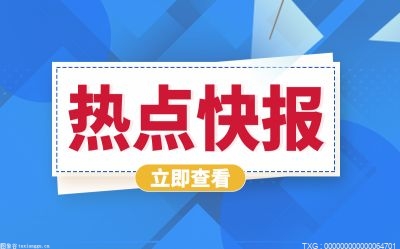仅仅在北京,这个城市就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1048家,占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量的29%,位列全国第一,同时,北京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人才超4万人,占全国的60%。
我们拥有如此多的AI企业,为什么我们对AI的商业成就的认知感并不强?为什么我们只读到天文数字的“预计市场规模”,但很少看到AI企业有漂亮的财务报表?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如今的AI行业进入越亏越烧——越烧越亏的循环,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,也一直在总结一些结论,如这些企业商业化的共性问题是诸如技术能力有限、缺少通向行业的痛点清单、实用人才的匮乏等等……事实上,这些问题都存在,而且本文也要进行详细的记述,但是这似乎不完全是问题的终极答案。
直到做完了对圈内十几位专业人士的深度调研,笔者才发现,问题的根源,可能源自我们对于AI落地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认知错位,进而决定了大多数企业的路径和资源的错配,这才是根本性的原因。
阅读提要:
01技术和工程,孰轻孰重?
“我们的规模虽然目前并不大,但我们是一直创造正向价值的并植根于实践的,我们的努力没有被束之高阁,而成了有创新价值的产品”,这是曾任微软雷德蒙德研究院深度学习技术中心的首席研究员、现任京东集团副总裁、京东AI研究院执行院长的何晓冬一直颇感自豪的事。
相对于其它几家互联网超级平台的AI研发规模,何晓冬所在的部门只有数百人,而他们的研发方向也很具体——对内依托京东的用户规模优势,不断的优化智能客服的能力,对外把这种能力做成产品卖出去,应用在诸如智能政务热线、智能外呼、数字人、智能营销等语音语义场景里。
“我们方向走的对,其实只有一个原因,就是搞清楚了我们能给市场带来什么价值,价值的核心点在哪里,然后用我们的工程能力搞定它”,何晓冬说:“脱离了价值锁定的AI研发是很酷,但很难有商业回报。”
在何晓冬看来,真正意义上的“科学原理意义上的进步”,只来源于两个渠道:“要么是对于大规模应用实践的规律总结,要么是极少数天才在很少外部资源的支持下的‘顿悟’,而前者是绝大多数非天才的必由之路”。
何晓冬举例说,如何制造一台光刻机——”所需要的任何数学公式、物理学定律和工作原理,都可以在任何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全,但是这距离制造出来完全是两码事,其间需要解决数以十万级的工程问题。”
如果仅仅从经历来说,马兆远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那种科学家,他是南方科技大学教授、英国物理学会会士,曾任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、更是深圳两化融合的首席科学家。
推动世界的绝大多数进步,首先是解决了工程问题,这也是马兆远的观点,他认为自己是“世界二流科学家,但更是个工程师。好的科学家应该是工程师,好的工程师应该是科学家”。
马兆远的观点很犀利,他认为:“科学是第二性的,工程才是第一性的。科学家解决可能性问题,而工程师解决可行性问题。”
对于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的高端制造业升级,马兆远认为,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升级,包括参与工业4.0,提升高端制造业的研发、生产水平等等,需要的首先是工程能力,是价值实现的手段问题,他说:“产业的真实进步,每一步改进,都意味着大量的选择和优化,而这是在实践中大量开发经验和工程训练积累而成的能力。”
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进步,反而是“需要大量工程沉淀,在充分的工程文明基础上,科学文明自然地发生”。
而纵观我们的AI企业,不缺乏的从来是讲故事的能力,更不缺乏的是发论文的能力,但是对如何解决问题却语焉不详,或即使有案例说明,也只有前因和后果,而独独跳过了其中的工程环节。
而这种“跳过”并不是因为商业上的保密,而是因为乏善可陈,马与何两位的观点重合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,AI企业不仅要了解科学、懂得技术,更重要的是知道痛点何在、价值何在,“并进行真正能把构想和创意造出来的创新型工作”。
而在笔者看来,这种辨析,才解决了AI商业化命题中的第一性原则,而我们的大多数AI企业,似乎把两者颠倒过来,所以我们看到的企业请的科学家越来越高级、发的顶会论文和拿回来的国际奖项越来越多……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的AI能力不断增强,但这似乎又无益于企业的商业变现。
该是解开这个悖论的时候了。
02管理者是第二个问题
在AI的商业化落地中,排在第二位的重要因素,同样是非技术问题,严格说,是一种管理者问题,或者是管理者的认知问题。
目前,中国AI企业最希望打开的是大型企业市场。利润尚在其次,主要是大型企业的示范效应很强,一个大型企业打开局面,就可能意味着一个行业对AI敞开大门。
行业里盛传的故事是,在某个重要的会议上,一家AI企业的负责人恰好与一家超大国企的负责人同车,于是顺便安利了一下自家的AI技术,遂拿下千万级的大单。
从大型企业的局中人,和局外人看来,对这个故事看法截然不同。
”这其实才是正确的打开大企业AI市场的做法,就是一定让一把手有感知、有认同“,笔者拜访的某特大企业的一位中层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:“其实,就是两个人不同车,也可以想办法安排同车,或者安排在某个场合见面,这比什么推广的效果都要好”。
这个说法可能让一些AI企业不爽,但笔者采访的绝大多数特大型企业的AI业者却基本形成共识,他们指出,大型企业要落地一项全新的技术,最好的办法是自上而下,而非自下而上。
一个特大型国企落地一个新技术体系,本身就很难,特别是前沿的数字技术。
绝大多数特大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都很早,多年来的累积建设,如同叠屋架床,体系非常复杂。如果是在体系外围做单点式创新还不算难,但如果要把AI技术融入大企业、大行业的技术底座,其复杂性难以想象,其失败也是有一定概率的。
举一个非AI的案例,当年阿里为了推广钉钉,不但马云直接找到了复星系的掌门人郭广昌,甚至还把钉钉做成了定制版的”复星通“。即使如此,一个协同软件也在复星体系内三年才基本铺到基层单位,而AI落地的难度远非钉钉可比。
“特大型企业负责人要考虑的问题很多,而很多问题本身是矛盾的,没有绝对的最优解。所以没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,就是他们很难做决定的问题。这时候你就要灌输认知,但其实特大企业的一把手,对于互联网巨头的掌门人的认知度并不高,信赖成本很高”,一位业者这样告诉笔者:“认知度不高,你还不主动接触,不做说服工作,怎么能让人下决心?”
笔者访问过的几乎所有特大型企业的AI负责人基本都是同样的观点——特大企业规模化上马AI,一定是一个“一把手工程”,不是99%,而是100%。
但他们也承认,对如此复杂的体系性问题,很难通过一次对话解决,但“如果你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,就更不要想拿下订单了”。
插一句,对于这个结论,很多非体系内的业者并不认同,例如前文叙及的何晓冬博士,他就认为:“刷脸营销是不可靠的,可以偶尔为之,但主要还是靠提供对方需要的价值。”
都没错,但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,就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。从目前来看,恐怕还是要遵循大型企业内部人士的视角,才更为切实。
接下来,几位大企业内部人士的另一个观点让我更感震撼,他们的观点是:“AI能否进入企业的考虑目标,取决于高层,但是否能落地成功,取决于执行层是否倾力支持,而最大的阻力,就是中层的技术骨干。”
“中层其实是最保守的,因为他们是最实际的。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对保守,最大的诉求是维护既得利益,所以做体系性调整中他们的阻力最大”,受访者告诉我:“一个中层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个技术条线,而整个一个技术条线的消极配合,就绝对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。”
当然,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是从个人考量出发,而是站位决定了保守,“对于很多成熟业务来说,用传统的方法已经做到了极致。这时候,要你去接受一个新的技术,而且是不成熟的、需要不断调整、优化,而且优化的权力和能力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技术,大部分中层骨干会选择说不”。
对于AI应用,很多企业里发生的现实就是,高层难以接触但未必排斥,基层年轻人大多欢迎、热爱新技术,真正最难说服的是掌控实际业务的中层。
03 走出AI落地的新路径
关于AI企业的技术能力,其实一直以来缺乏评定的标准。因为公司毕竟不是学术机构,参加顶会、发表论文这些标准只能参考,不能转化为直接的销售动能。
所以,这部分的采访,笔者除了采访技术人员外,还采访了销售和服务环节的从业者。你也许会觉得奇怪,为什么技术问题要去采访销售和服务环节的人?
因为只有他们对于技术的落地和后续的服务感触最深。
什么是AI企业最需要的技术能力?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两部分,即技术能力和服务于客户的业务能力,后者是前者的延伸,但并不是前者解决了,后者就一定能自动解决。
目前AI商业化落地的最大困难,是没有一条高效率、低成本,而且可以大规模复制的赋能方式。
而大家知道,数字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可复制,一个数字产品的虚拟化拷贝可以服务于数亿人,但边际成本极度接近于零。
但是,在目前的AI领域,却很难出现这样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,反而体现为应用的越深,边际效益却无限的增加的问题。
从表层看,这是AI模型的通用能力和专用能力之间的矛盾。
绝大多数的用户企业都不具备独立打造模型或者算法的能力,因为不但门槛极高,而且几乎没有边际效益,所以从AI通用型企业购买服务是主流方式。像百度这样的AI头部企业也是着力在打造通用化AI能力。
我们再回想下,早年买电视的时候,甚至调试天线的位置,都需要人爬到屋顶上;或者我们早期买电脑的时候,会不明觉厉的看着带着一叠软盘在BIOS界面上运指如飞调参数的工程师。
今天,我们使用电脑,其实只要掌握开机、关机和连上wifi就可以了,这就是技术应用的进步。
而AI的模型复杂程度虽然远非家电、电脑的调试可比,但道理是一样的,目前的人工智能模型本身并不“智能”,它需要经过复杂的调试和预训练才能够使用。
比如,制造企业里的生产安全监测,算是最通用的场景了,但它的落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比如我拜访的一个AI架构师,他所在的企业的生产场景,是在深深的地下、复杂的地层中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,网络信号无法传输,需要配备边缘算力的摄像头,或者需要有线传输,这成本可就高了……更严重的问题是,生产环境中油性颗粒和烟尘含量很高,再干净的摄像头,用三天就彻底“糊了”。
最后,这个项目面临的选择是,要么放弃;要么产生一条新的工序——工人必须每三天清洗一次摄像头的外罩。
而这仅仅是最简单的,还不涉及到核心技术问题,仅仅是外部变量问题的AI落地难点。
远远比这艰难的是,真正给传统的高技术产业赋能。
所谓的传统的高技术产业,就是石油、海洋监测、卫星、核能这些行业,它们本身的技术壁垒极高,AI行业的从业者很难从外部获取足够的知识来设计通用模型。
比如石油行业,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傻大黑粗的土豪行业。其实,石油行业在国内应用计算机的历史,可能比军工行业都早。
石油行业的一个最典型的场景,是通过制造人工地震,用仪器回收地震波,再根据波形还原地形构造从而找油,被形象的称为“给地球做CT”。
这是一个超级吃算力的行业,是一个最早拥有行业超算中心的行业,也是一个数字化程度很高,人工智能可以大有作为的行业。
与之相似的还有卫星行业,你可能不知道,我们头顶的数百颗卫星,每天至少下传100TB级别的数据,而其中传统用户如国土资源、海洋监测、农田监测等等,只能用到20%的数据。
这个行业与前面的石油行业的类似之处在于,每天产生海量的数据和图像,但这种图像的识别高度的非智能化,只能在计算机辅助下通过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眼识别。
这也是一个让AI行业人士兴奋不已的领域,要知道CV(计算机视觉)可是和NLP(自然语言理解)相媲美的人工智能前两大应用领域,是最成熟的领域之一。
非常多石油、卫星领域的行业人士,都希望通过计算机视觉来解决读图问题,用他们的话说,哪怕只有80%的准确率,也可以把现有数据的利用率从20%提升到50%,相当于生产力提升了2.5倍。
但是,非常智能、也非常成熟的AI,偏偏在这个领域铩羽。
其实,真正困住AI企业的,就是这类行业的传统高技术壁垒。
无论是地震波的收集工具,还是卫星上的各种可见光、非可见光传感器,都有一个特点——标准化程度很低。
比如石油行业的某种图像格式,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在行业内很盛行的西方某国的中小企业开发的专用仪器生成的,因为好用,一直用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在用。
但对于通用AI企业的人来说,他们几乎没有可能知道这家公司的存在。很大概率是,这家公司可能已经不存在了。
我见过不止一个石油行业的人士向AI公司的人抱怨:“你们的模型,连我们基本的数据格式都无法导入,我们怎么用呢?”
所以,一位业者这样对我说过:打造垂直行业应用的难度,和它的收益成正比。越难的事情,你做成了才有独特的价值。我们需要AI企业的人有一种助手的心态,和我们并肩工作三年、五年,把我们这个行业真正弄懂了,才能拿下大单。
是AI企业的人傲慢么?其实他们也一肚子委屈,因为他们根本没法派出大队人马去服务,如果真的如此,结果可能是天价。
我们看多了“AI企业深入产业内部,携手寻找行业know-how”之类的报道,但其实这类事情极少发生,或多发生于开拓某个行业的早期,或者是老板亲自盯的项目。
更现实的情况是AI企业的工程师几乎与被服务企业的人连面都没见过。
为什么?因为真正的、优秀的算法工程师、架构师实在是太贵了,如果以他们的薪酬来计算服务费用,所有的订单都是亏损的。
行业里盛传的“一次派出几十个工程师,自己掏钱住酒店,走的时候连客户的打印机都修好了”的段子,据说就是某H企业攻掠AI市场的方法,但这的确是用亏损换市场,不走寻常路。
对于正常的AI企业,重头的开销本来是在研发上,可事实教育之下发现,更多的费用其实产生在销售和服务环节。
于是,ISV模式大行其道。所谓ISV,英文全称是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s ,意为“独立软件开发商”,原本特指专门从事软件的开发、生产、销售和服务的企业。但这个词在现今的语境下,特指通过“被集成”方式,为开放接口生态下的用户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公司。
原本,ISV是一种正常的、合理的商业现象,因为人才本身是分层的,人工智能模型也是一种产品。但是,就像你买一台空调,去给你安装的人,对空调的理解并不用达到空调设计师的程度。
但AI企业的特殊性在于,ISV的能力程度,虽然不需要高到算法工程师的程度,但也不能降到空调安装工的程度,他们需要相当了解AI,能独立协助用户优化,最终达到合格交付的水准。
笔者没有调查过海外的ISV市场,所以无法对比,但至少在本次调查中接触的企业,对国内ISV的评价普遍不高,认为他们“不会做比及格线高哪怕1分的事情”。
这话可能偏激,但有个用户企业给我讲了一个实际故事——某个业内盛传的AI智能客服大单,就是因为ISV缺乏足够的责任心(或者是业务能力的不足),使得精心开发的模型在实际落地中,并没有足够的优化和升级到位,最终使得用户单位极不满意,第一单,就成了最后一单。
但你要全怪ISV也不行,这个行业有两个特点。
第一,大部分ISV的利润并不丰富,客户黏性也很低。所以绝大多数ISV的结果都是长不大,刚刚够自给自足,这样的企业很难有足够的雄心把服务做好,因为前途不大,不适合有足够野心的创业者,所以也难以内生强大的变革动力和把服务做好的决心。
第二,虽然这些ISV不好用,但现实状态是,随着产业级数字技术的普及,各大巨头都需要大量的ISV去做落地,在这种情况下ISV虽然前途不大,但生存压力也不大,企业也很难苛责他们。
可以看到,传统软件时代的“顾问咨询-交易成单-软件实施-软件交付”的业务流程,高度定制化、非标化的特点,并不适用于产业互联网,因为后者本身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降低服务成本、降低人力支出,所以才有了云计算、AI乃至于PaaS、SaaS等概念,它们的出现本身是为了降本增效,但其落地环节却成了降本增效的最大门槛。
这就是AI落地难的商业现实,有人总说,中国的AI行业缺的是ChatGPT这样惊艳的发明和创新。但笔者认为,这种惊艳之作固然对人类的意义极大,但创造一种更简便、更普惠、更低成本的把AI落地于千行百业的技术范式或者商业范式,可能难度和意义都更大。
04 结语
其实,AI的商业化落地的难处,还远不止以上这些。
比如,在人才侧,传统的企业对于AI人才来说,培养难、招聘更难。一个高铁行业的朋友就告诉我,按照铁路的机制,最接近AI实操的是各铁路局、机务段,但在整个铁路都是亏损的情况下,这种基层的单位开出的薪资,都很难吸引到哪怕是一个AI专业的应届生。
还有,AI落地的成本高,短期内收益低,决策者要承担的成本高,推行的阻力大等等。
也有人认为,技术的问题,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。例如,近年来低代码、零门槛的AI工具也大行其道,不乏普通的铁路工人、大学生、AI爱好者利用这些工具独立开发出好的AI应用的案例。
确实,开发一个简单的模型不难,但真正能发挥AI核心价值的,如前述的石油、海洋、卫星、核能等高技术壁垒的行业,才是能够真正放大AI价值,使之成为国之重器的领域。而这些领域的技术深度,绝非工具层面可以解决的。
但笔者还是相信,AI行业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,就像ChatGPT出现前,我们无法想象人工智能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,AI在能力上的储备已经到了从缓慢溢出,即将变为喷薄而出的阶段,高科技行业有自己的规律,也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商业化未来。